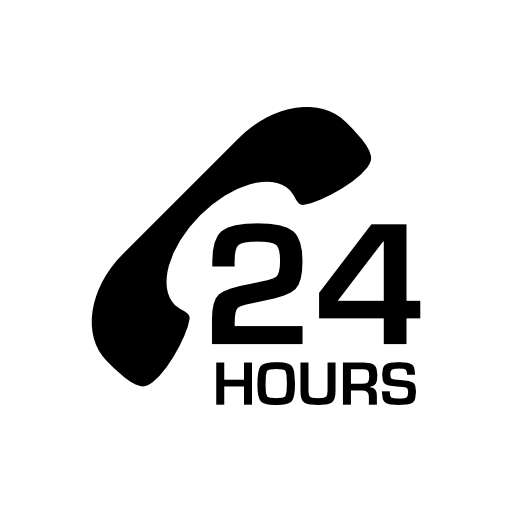照片上的人叫陈雷,是阿拉善边防旅的军人。四年前,他是高考670多分的理科状元,是中国人民国防科技大学的高材生。四年后,戈壁风沙把他从一个青涩少年,打磨成了健硕挺拔的排长。
那是我第一次走进清河口采访。那天我跟随陈雷带领的2排,进行了陆路巡查。途中我们找了个背风的沙山进行短暂的休整。吃饭时,我想做现场采录。可几个战士一说话,嘴唇就因为干裂,迸出一粒粒血珠。陈雷说:“还是不要讲太多了,大家平时都跟家里说,这儿啥都好。要是一报道,让爹妈知道了,还不得心疼死”。这话也许说到了大伙心里,战士们低着头,使劲吞咽着干燥的压缩饼干,沉默了下来。陈雷又说:“咱当兵的流血流汗不流泪,来,唱支歌!”
接着,他就带领战士们唱起了这首清河口的连歌。一唱歌,几个战士的嘴唇又裂开了。我本想阻止大家别唱了,可又想把这首歌录下来。只听歌词里唱到:“我当兵就在清河口,站成八千里边防线上最西的高峰”。唱完了,陈雷说:“哭了,唱了,该干啥还得干啥。”说完一九游体育官网挥手,巡逻的脚步,又闯进了烈日黄沙之中。
在内蒙古漫长的边防线上,我还有过一次最刻骨铭心的采访。那是在2016年,我追寻着一个叫“杜宏”的名字,走进了被誉为“北疆第一哨”的伊木河。
杜宏,曾是伊木河边防连的连长。在祖国最为寒冷的额尔古纳界河畔,他戊守了整整13年。2015年12月30日午后,刚刚过完31岁生日的杜宏,在检查哨所途中,因雪大路滑,山路陡峭,从26米高的悬崖处跌落。那天伊木河的温度,是零下57°。当战友们找到他时,杜宏身旁殷红的鲜血早已结冰。他牺牲在了2015年最后一抹夕阳里。
当我们的采访组到达伊木河的那天傍晚,气温骤降,天寒地冻。大兴安岭深处,哨所的悬崖下,连队战士们整齐列阵,向着如血的残阳大声呼喊“连长……连长……连长……”
此念向北。从伊木河回来,坐在电脑前,整理着几十个小时的采访素材。杜宏和战士们的声音,响彻凌晨的机房。听着他们的声音,我仿佛就能看到那一张张稚嫩的脸庞,和那些清澈的眼神。
转眼7年多时间过去了。那次采访之后,“边防”,就再也没有走出我的生命。从此我有了浓浓的军旅情结,每到年节,我和战士们也都会通个电话,道声平安。当年采访结识的年龄最小的新兵,今年也要脱下军装,离开连队了。电话那边,他们哽咽着告诉我:“豆豆姐,我们舍不得离开。”
大国之门,需大国之士守卫。大国之士,要有大情怀大担当。在亲人眼中,他们都是孩子,但在国土之上,他们是坚强的卫士。
这位战士和杜宏是同年的兵,他叫张良,长眠在阿拉善的大漠戈壁深处。2002年,张良与杜宏从新兵连告别,奔赴了内蒙古一东一西的两个哨所,分别驻守在八千里边防线的两端。如今,烈士长眠,可英魂仍然守卫着北疆安宁。
去年,我又一次前往清河口采访。在514号界碑旁,见到了这位“年轻”的老兵。墓碑上的照片里,永远19岁的张良依然稚气未脱。当年,入伍仅153天的张良和战友们徒步巡逻8个多小时后,把仅剩的半壶水留给中暑的战友,自己返回连队请求支援时,因中暑缺水而牺牲。直到今天,清河口哨所还保留着张良的床铺,每次集合,呼点的第一个名字,就是张良。
张良离别战友的时间是2002年5月14日。那一年,中蒙联合勘界完成。在张良牺牲地以北不远处,重设了界碑,界碑自然编号514。部队在张良牺牲的地方为他修建了烈士墓,立起一块碑。从此,大家就把张良的墓碑称为“清河口的第23块界碑”。
从零下57度中国最冷的“雪域孤岛”北疆第一哨伊木河,到“生命禁区”内蒙古西部第一哨清河口。千山万壑之间,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艰苦卓绝,印刻着边防军人的奉献担当。
北疆正芳华,我的身后是祖国!此时此刻,我的耳边还会响起陈雷和战士们那首伴着风沙唱响的连歌。而那些迎着烈日巡逻的画面,也依然清晰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。让我理解了青春芳华的另一种含义。
采访中,有一位年轻的女兵告诉我,她的姐姐每走到一个地方,都会给她寄来一张明信片,上面写着:“看,你用青春守护的国家,一切安好!”